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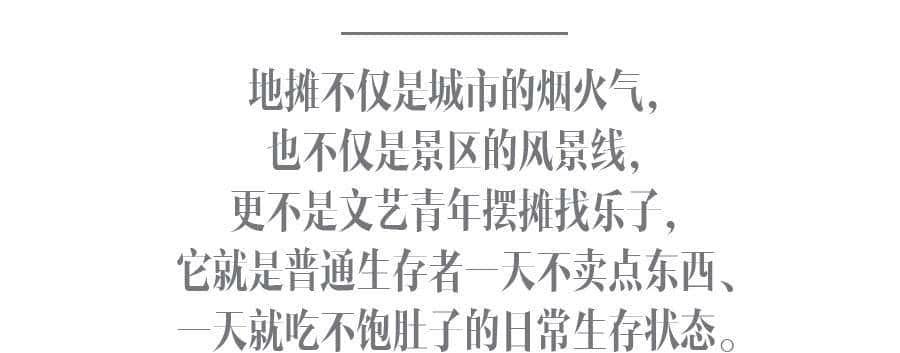
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是从“地摊文学”开始的: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和金庸的《神雕侠侣》放在一起;间或有加斯东·巴什拉的《梦想的诗学》与亨利·米勒的《情欲之网》。它们摆在河道市场的一侧,几近干涸的溪流在水泥封固的河床中间象征性的流过。四周的天际线是“三线建设”选址的巍峨群山,汽车工业就隐藏在中国腹地山间的各个沟壑里,这个在古老汉江边上的新兴城市,也因此被称为车城。
这是1990年代的场景,事隔二十多年了依然记忆犹新。许多与我一样的70后,在大学校园里为一个更好的未来奋斗。一部分人专心致志地攻读专业;一部分人爱好足球,每周都买《体坛周报》;一部分人开始混迹社会,传销也不免侵袭到大学校园,我甚至也去听了几堂课,唯一的收获是如何克服羞涩。
走到大街上,银行铁拉门上的横幅召示着金融和骗术交相生成,内容大致是“清理三角债”、“禁止高息揽存”、“防止民间高利贷风险”之类的。那时刚刚有传呼机,许多人能快速收到股票的动态,似乎发财的美梦就在不远的前方。
无数的文学描绘过“都市化”的场景,作家们刻画了一个感官世界和可以达到的未来。司汤达在《红与黑》中,描述了于连从外省到巴黎的一系列命运转归,他的出身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地摊货”,父亲是木匠,而他在家里因不会干活而被瞧不起。但于连终于因引荐而好运连连,他跻身上流社会的餐桌与榻边,并且以征服女人为乐事,不过最终的结果却被上流社会的阴谋所挫败,误了区区性命。

1997年上映的《The Red and The Balck》电视剧版,Kim Rossi Stuart饰演于连 图片:On Being Wild
背景、出身,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其重大的资源。恰恰不幸的是,于连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,不过他却缺少这种资源,又有谁可以甚至真诚地庇护他呢?
这就象“地主”和“地摊主”是两个概念一样。地主拥有自己的产权,他可以出租,收割,躺在地契上睡大觉。而地摊主十分可怜地拥有两个平方米的临时经营权,他的一切经验都建立于这个两平方米之上。他不仅要应付流动顾客的各种“检选”,同时还要预防城市管理者对他临时权力的剥夺与收回。于连最终成为上流社会的弃子,源于他毫无根基,除了一腔热血与显而易见的才华之外,他还有什么可以使人不加害于他的呢?
“都市化”是“现代性”的一大主题,在作家的心目中,都市化是海明威笔下的《流动的圣宴》,是福楼拜笔下那个包法利夫人所寻觅的贵族领地,也是菲茨杰拉德在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所津津乐道的上流社会。不过“都市化”又有另外的一面,它需要一个庞大的劳动力阶层为其提供设施与服务。如果“都市化”把这样一个阶层都赶出去,或者抽干了,那这样的“都市化”不过是塑料花一样的干燥和无趣。

海明威在书中《流动的圣宴》提到过的巴黎街道Rue Mouffetard 图源:LULU Escapes
无论是在经典小说还是在对过去现实的温故中,我们都能发现一个真理:时代似乎揭开了崭新的一页,但又实际上一切都在自我重复之中。至少“地摊”消亡的速度,不至于让我们觉得很悲观。
这就像中国的农民,不管去了哪里,只要没人管,就会开辟一块菜园,或是种点庄稼。地摊就是城里低收入者的自耕地,一有风吹草动,就不见了;可一旦没人管,就又各有各的活路。
既便肃清了城市道路边上的所有障碍,“地摊”依旧顽固地存活于网络之中,那些在网上开网店的小业主,在没有做大的情况下,也不过是“网络地摊”的一种形式而已。他们叫卖的吆喝声变成了朋友圈、亲友团。
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来看,“地摊”应该放到哪个版面?是“民生版”、“经济版”还是“娱乐版”?显然,地摊经济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,地摊谈不上经济,它的规模或许可以很大,但它又是微碎的,很难成为一个集团。反而是为地摊服务的经济,成为一时的热点,如在香港上市的五菱汽车,所设计的“地摊车”便供不应求。这就像挖比特币的人没赚到钱,卖挖矿机的人却赚到了;做直播带货的人没赚到钱,卖直播灯的人却赚到了。

6月4日,山东省青岛五菱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展示了“地摊车”的后车厢。图源:Caixin Global
如果把“地摊”放进“娱乐版”,就多少有拿人家的生计开玩笑或借机取笑与自嘲的恶趣。当然,人活着有各种不易,借此机会拿他人或自我开涮一下,也未必不是社会情绪的“减压阀”。不过如此以来,则容易让我们忽略掉那些视此为正经营生的穷苦个体,他们被中等收入者的娱乐的、虚假的信息所掩盖,而他们真实的诉求与声音,则几乎没办法传递出来。
所以说,对于一个严肃媒体而言——如果还有的话——则应该将关于“地摊”的信息传达放在“民生版”。它不仅是城市的烟火气,也不仅是景区的景色线,更不是文艺青年摆摊找乐子,它就是普通生存者一天不卖点东西、一天就吃不饱肚子的日常生存状态。
摆地摊用经济手段是行得通的,但搞经济用地摊手段是行不通的。经济要搞好,不是导流、不是推波助澜,也不是催生热点。有热点就有冰点,永远有你关注不到的事情,那还不把自己累死。倒不如开放,引入自由竞争。让市场这个“看不见的手”去进行自我调节。如此以来,资本、人才流动的效率反而最高。
不过,一代人的宿命纠结于天气与地摊,这是必然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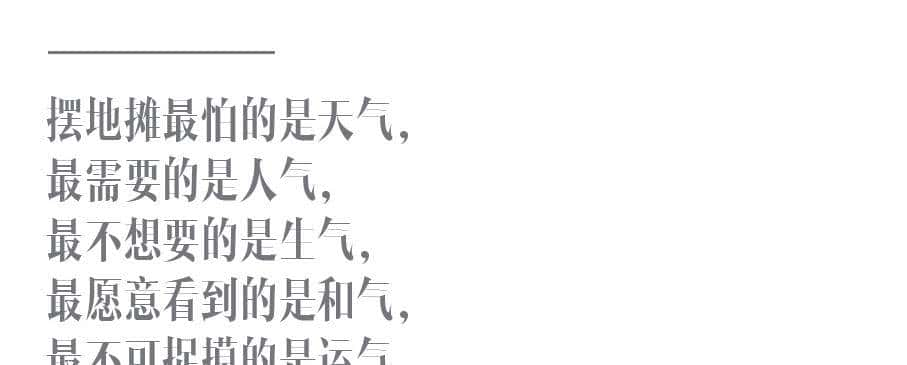
目前,摆地摊的人运气来了:他从未获得过如此高的曝光度;也从未想过上市公司也会来蹭流量;装穷、哭穷、嘻嘻哈哈的人也跑过来凑热闹;甚至也会影响到股市和大量相关的题材。
难道说我们在被互联网绑架的同时,也不得不被“地摊”绑架吗?就像前一轮失业潮时,我们鼓励万众创业,自己养活自己、彼此养活彼此。这一轮失业潮,也许“地摊”将成为一个最大的关键词。
必须记住的是,当我们回忆起歌颂伟大的互联网时,回过头来发现它不过是一门生意。互联网正在抹平一切生态和业态。它由早期的“工具型”向中期的“统治型”发展,未来会出现“垄断型”的局面。这是借用波斯曼在《技术垄断:文化向技术投降》中的分期。

尼尔·波兹曼(Neil Postman)1997年在杜佩奇大学关于《技术垄断:文化向技术投降》的演讲 图源:College of DuPage/YouTube
我们的互联网所鼓吹的迭代,不过是试错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变革,不过是优化体验和增加自动化效率。互联网的飞速发展,不过是为了跑到规则制订者的前面,并且希图自己成为规则制订者。
一边是互联网引领的人工智能前景,一边是楼底下摆地摊的艰难岁月。正是在这样魔幻现实的双重场景下,我们发现有些东西在变,而有些事情,根本没变。
波斯曼忠告说:“至少对所谓进步观念抱怀疑态度,不把信息和理解混为一谈。”如果我们渴望“现代性”,进入一个现代性的国家,拥有令人迷醉的都市化生活,并且,哪怕渴望成为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时,我们也依旧要怀想波斯曼所说的:“理解神圣和世俗的差别,不会为了追求现代性而漠视传统。”
“地摊”在我们这个世代扮演了贫富差别分界线的角色。也是富人为穷人留下的应许之地。目前看来,假若没有当年“地摊文学”的哺育,一个作家的成长与发育,或许也会迟缓许多。如果我们目前仅仅在概念上去辩析利害与好坏,如果我们遗忘那过去的温情记忆,我们的传统也会更快速地消亡,直至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铲除的。

肯尼亚内罗毕的街边书摊 ,这些书摊一般位于市区繁华街道上。图源:HapaKenya
对于我个人而言,我更早的记忆停留在妈妈领着我和弟弟去县城,我们在半路上走累了,找到一个摆馄饨摊的地方坐下来。和《一碗阳春面》中的情景很像,我们三个人吃了一碗馄饨,而且每个人都说自己吃饱了。那种因匮乏而产生的深刻记忆,以及那种因吃不饱而产生的美味幻觉,竟然会相伴于一个人的一生。
经济指标是粗暴的,它必定会剥夺人内心的幸福感。不管给国民发多少钱,或是提高多少的福利,他是永远嫌少的。这是一条不归之路。谁也没有办法停止。尤其是专家发现,每一次印钞票,都会导致贫富差剧进一步加大。
最要紧的,是我们要关注街头的每一个路人,我们要尝试理解他。这需要一种关怀的本事:如何把一幅世界地图看作是一个地摊而已。

撰文 胡赳赳
编辑 Chris Wu
头图/封面 MUNIR UZ ZAMAN/AFP |
Getty Images
编排 Claire

Copyright © 2020 WSJ. China. All Rights Reserve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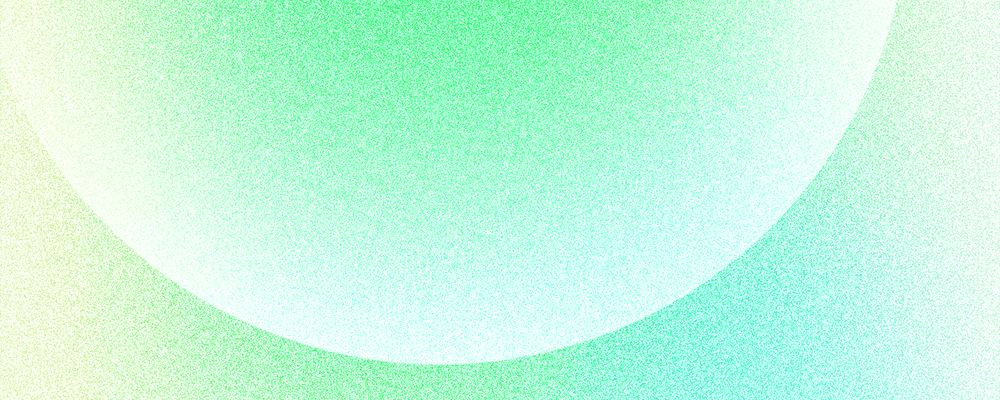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暂无评论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