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了趟山西大同,感觉这里和网上说的不一样,3个疑问有知道的吗
引子
面馆里的热气,熏得我眼睛有些发涩。
我低下头,假装在看手机,实则是在看斜对面那桌客人碗的边缘。一圈蓝色的花纹,和我手机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。就是这个碗,把我从一千多公里外的南方城市,拽到了这个叫大同的北方古城。
心,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,一阵阵地发紧。
手机屏幕上,是我老婆王淑琴三天前发的朋友圈。九张图,配文是“公司团建,放松一下”。其中一张,她端着一碗面,笑得比窗外的阳光还灿烂。背景里,正是这个蓝边碗。定位显示的是邻省的一个著名景区,可我知道,她在撒谎。
我放大另一张她拍的窗外街景,通过一个模糊的店铺招牌,用地图软件搜了整整一天,最后找到了这里。山西大同,永泰街,老冯面馆。
二十多年的夫妻,我以为我们之间没有秘密。她温柔,贤惠,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,把我和儿子照顾得无微不至。我是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部门经理,工作忙,压力大,是她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港湾。可目前,这个港湾似乎要塌了。
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嘶吼,为什么?为什么要骗我?
来大同之前,我查了她的通话记录。一个陌生的号码,归属地就是大同,最近一个月通话频繁,每次都在深夜。我不敢想下去,那种背叛的刺痛,让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,在深夜里辗转难眠。
我必须来。我得亲眼看看,到底是什么人,什么事,让她编出这样拙劣的谎言。
内心独白:老李啊老李,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一把年纪,还学年轻人玩跟踪。可不来,我这心里就像压着块石头,喘不过气。二十多年的感情,难道说就这么脆弱吗?我不信,我非要弄个清楚。
面馆的门被推开,风铃叮当一响。我下意识地抬头,心跳漏了一拍。不是她。我自嘲地笑了笑,怎么可能这么巧。她或许早就离开了。
我付了钱,走出面馆。外面的天很蓝,蓝得有些不真实。街道干净得不像一座传说中的“煤都”。路边的老人悠闲地晒着太阳,下着象棋。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和,和我内心的狂风暴雨格格不入。
我手里攥着一张纸条,上面是那个陌生号码的主人信息。赵刚。一个陌生的名字。地址是红旗工厂家属院。这是我托朋友费了很大劲才查到的。
目前,我就要去见他。不管结果是什么,我都要一个答案。我拦了辆出租车,声音有些沙哑。
“师傅,去红旗工厂家属院。”
司机很健谈,问我是不是来旅游的。我胡乱应付着。车窗外,古老的城墙和现代的建筑交错而过。这座城市,和我想象中黑乎乎的样子完全不同。它很开阔,很大气。
内心独白:来之前,我把大同想成了一个充满谎言和背叛的灰色陷阱。可眼前的景象,却让我有些恍惚。难道说是我错了吗?不,那个蓝边碗,那个电话号码,都是铁证。王淑琴,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
车子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停下。红砖墙上,“红旗工厂家装公司”几个大字已经斑驳。空气里,似乎还弥漫着上个世纪工业时代的味道。我的心,又一次悬到了嗓子眼。深吸一口气,我推开车门,走了进去。那个叫赵刚的男人,就在这里。我的审判,也即将开始。
内心独白:我该怎么开场?是愤怒地质问,还是冷静地谈判?我甚至想过,如果他敢挑衅,我就和他打一架。可脚踩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,我只感到一阵茫然和无力。我像一个迷路的孩子,找不到回家的方向。
第1章 寻不到的旧地址
红旗工厂家属院比我想象的要大,也更破败。
几栋五层高的红砖楼,墙皮大块大块地脱落,露出里面的水泥。阳台上堆满了杂物,几根晾衣绳横七竖八地拉着,挂着洗得发白的衣物。
我按照纸条上的地址,找到了三号楼。楼道里光线昏暗,空气中混杂着潮湿和油烟的味道。我一级一级地走上楼梯,皮鞋踩在水泥地上,发出空洞的回响。
四楼,402。门是那种老式的绿色防盗门,上面的油漆已经裂开,像老人的皱纹。我站了很久,手抬起来又放下。
内心独白:敲开这扇门,我可能会看到最不想看到的一幕。王淑琴会不会就在里面?她看到我,会是什么表情?惊慌?还是愧疚?我的心像揣了只兔子,怦怦乱跳。
最终,我还是敲了敲门。咚,咚,咚。声音在安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突兀。
没人应。我又加重力气敲了几下。还是没动静。我把耳朵贴在冰凉的门上,里面死一般地寂静。
难道说人不在?或者,地址是错的?
我下楼时,碰到一位提着菜篮子的大妈。我走上前,挤出一个笑容。
“阿姨,您好。跟您打听一下,这402住的是不是叫赵刚?”
大妈警惕地上下打量我一番。“你找他干啥?”
“哦,我是他一个老朋友,从外地过来,想找他聚聚。”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真诚。
“赵刚?”大妈想了想,“哦,你说的是老赵家的儿子吧?他们早就不住这儿了。得有七八年了吧。”
我心里一沉。“那您知道他们搬去哪儿了吗?”
“这谁知道。这片区要改造,好多老邻居都搬走了,早就没联系了。”大妈摆摆手,提着菜篮子颤巍巍地上了楼。
线索,就这么断了。我站在院子里,看着斑驳的红砖楼,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挫败。就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,使不出一点力气。
我不甘心。我又在院子里转了转,找了几个正在下棋的老大爷打听。他们对“赵刚”这个名字没什么印象,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年轻人了。
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大爷嘬了口茶,慢悠悠地说:“红旗厂早就倒闭了。年轻人要么出去打工,要么就自己找活干。你说的这个人,说不定早就离开大同了。”
离开大同了?那淑琴为什么来这里?
内心独白:难道说一切都是我的胡思乱想?可那个电话号码,那个谎言,又怎么解释?不行,我不能就这么放弃。我必定要找到他。这件事不弄清楚,我们这个家,就永远有个疙瘩。
正当我一筹莫展时,旁边一个看棋的大叔插了句嘴。
“你说赵刚?是不是以前在厂里搞技术的那个?他爸是咱们厂八级钳工,赵师傅。”
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,连忙点头。“对对对!可能就是他。您知道他在哪儿吗?”
“他爸走得早,听说他后来自己单干了。”大叔眯着眼睛回忆,“好像是在城西那边,有个叫‘北方机械’的旧厂区,他们几个老伙计在那里租了个车间,修一些老设备。手艺人嘛,总得有口饭吃。”
“北方机械?”我赶紧把这个名字记在手机里。
“嗯,你去那边打听打听吧。不过那地方偏僻,不好找。”大叔说完,又把注意力转回了棋盘上。
我连声道谢,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。虽然只是一个模糊的线索,但总比没有强。我走出家属院,阳光照在身上,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。
我叫了辆车,直奔城西。一路上,司机都在抱怨那个地方有多偏,路有多难走。我的心也跟着车子的颠簸,七上八下。
车子开了将近一个小时,最后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前停了下来。司机指着远处一片锈迹斑斑的厂房说:“就那儿了,车进不去,你自己走过去吧。”
我付了钱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走。空气中弥漫着铁锈和机油混合的味道。这里比红旗厂还要荒凉,巨大的厂房像一头头沉默的钢铁巨兽,趴在这片土地上。
内心独白:王淑琴,你到底在图什么?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,跑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来,见一个修旧机器的男人。我真的不懂。我们之间,到底出了什么问题?
走了大致十几分钟,我终于看到一个厂房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牌子——北方机械维修中心。门口停着几辆破旧的货车。我的心跳,再一次开始加速。
赵刚,应该就在这里面了。
第2章 沉默的匠人
厂房很高,很空旷。阳光从屋顶的玻璃窗透进来,照亮了空气中飞舞的尘埃。几台巨大的、看不出用途的机器散落在各处,像一个个沉默的巨人。
“当……当……当……”
一阵富有节奏的敲击声从厂房深处传来,打破了这里的寂静。我循着声音走过去,脚步不由自主地放轻了。
在一个巨大的车床旁边,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背影。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,上面沾满了油污。他中等身材,背影看上去有些单薄。他正拿着一把锤子,专注地敲打着一个零件。
他敲得很慢,很稳。每一锤落下,都好像经过了精密的计算。那声音,清脆而坚定。
我没有出声,只是远远地站着。我想看清楚,这个让我妻子不远千里跑来相见的男人,到底是什么样子。
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,停下了手中的活,转过身来。
四目相对。
他大致四十多岁的年纪,脸庞黝黑,布满了风霜的痕迹。额头上有几道深深的皱纹,眼神却很亮,像黑夜里的星星。他的手上,全是厚厚的老茧和一道道细小的伤口。
他不是我想象中那种油头粉面的男人,甚至可以说,有些土气。但他的眼神很沉静,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。
“你找谁?”他开口了,声音有些沙哑,带着本地口音。
我张了张嘴,准备好的那些质问的话,突然一句也说不出来。我看着他那双满是机油的手,再看看自己白净而略显臃肿的手,心里忽然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“我……我找赵刚。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干涩。
他点了点头。“我就是。”
内心独白:就是他。这个男人,就是赵刚。我设想过无数次见面的场景,愤怒的,悲伤的,甚至是暴力的。可现实却是如此平淡。他太平静了,平静得让我感觉自己像个无理取闹的小丑。
“有事?”他又问了一句,语气里没有好奇,只有询问。
“我姓李。”我顿了顿,还是决定直接摊牌,“我是王淑琴的爱人。”
我说出“王淑琴”三个字的时候,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,想从中捕捉到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。
他的眼神闪动了一下,超级细微,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。那是一种复杂的情绪,有惊讶,有怀念,还有一丝……坦然。
他沉默了几秒钟,然后放下手中的锤子,用一块满是油污的布擦了擦手。
“哦。”他只是“哦”了一声,然后指了指旁边一张破旧的木桌。“坐吧。”
桌上有一个巨大的搪瓷茶缸,上面印着“劳动最光荣”。他拿起茶缸,给我倒了一杯水。水是温的。
“她……还好吗?”他问。
这个问题让我愣住了。我以为他会辩解,或者质问我来干什么。可他却像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,平静地问起了她的近况。
“不好。”我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两个字,“她骗了我,一个人跑到这里来。你说她好不好?”
赵刚低下了头,看着自己那双粗糙的手,没有说话。厂房里又恢复了寂静,只剩下远处偶尔传来的风声。
内心独白:他在想什么?是心虚,还是在盘算怎么应对我?我看不透他。这个男人,像他身后的那些老机器一样,沉默,坚硬,让我无从下手。我的怒火,找不到一个可以宣泄的出口。
“她来过了。”过了很久,他才缓缓开口,“前天刚走。”
我的心猛地一抽。“她来这里干什么?”
赵刚抬起头,看着我,眼神里没有丝毫躲闪。“她来看一位长辈。顺便,也来看看我。”
“长辈?什么长辈?”我追问道。
“我妈。”他淡淡地说,“她病了,在医院。”
我愣住了。王淑琴来看他生病的母亲?这算什么理由?
“你们是什么关系?值得她撒谎骗我,跑这么远来看你妈?”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八度。
赵刚没有被我的怒气质问,他只是平静地看着我,然后拿起桌上那个被他敲打了无数次的零件,轻轻地摩挲着。
“我们是老乡,也是……老朋友了。”他的目光落在那个零件上,仿佛在看一件稀世珍宝,“有些事,你不清楚。”
内心独白:我不清楚?对,我是不清楚。我不清楚二十多年的夫妻感情,为什么抵不过一个所谓的“老朋友”。我更不清楚,她为什么要对我隐瞒。信任,难道说就这么不值钱吗?
我站起身,感觉自己再也待不下去了。这个地方,这个男人,都让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压抑。
“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。”我盯着他,一字一句地说,“我告知你,赵刚。王淑琴是我的妻子。后来,请你离她远一点。”
说完,我转身就走。我没有勇气再看他的眼睛。我怕在他那双沉静的眼睛里,看到我自己的狼狈和不堪。
我快步走出厂房,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眼睛生疼。身后,又传来了那“当……当……”的敲击声,不疾不徐,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第3章 医院里的凝视
从城西的破旧厂区出来,我心里乱成一团麻。
赵刚的平静,和他口中的“看望长辈”,像一团迷雾,把我原本清晰的愤怒和怀疑都搅乱了。他说他母亲病了,在医院。这是真的吗?还是另一个谎言?
我不能就这么走了。如果这是个谎言,我就要当场戳穿他。如果这是真的,我也想看看,到底是什么样的长辈,能让淑琴如此挂心。
我在路边站了很久,最后还是决定去医院看看。我给大同的朋友打了个电话,让他帮忙查一下,最近有没有一个叫赵刚的人在为母亲办理住院手续。
朋友的效率很高,不到半小时就回了电话。
“查到了,市第三人民医院,神经内科,十三床。病人叫刘桂香,六十八岁。家属联系人,就是赵刚。”
挂了电话,我立刻打车去了市三院。
医院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,让人心里发慌。我找到了神经内科,在走廊尽头看到了十三床的病房。病房门开着一道缝,我悄悄地凑过去,往里看。
一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老太太躺在病床上,插着鼻饲管,双眼紧闭。床边坐着一个男人,正是赵刚。他正拿着一个苹果,用一把小刀,一点一点地削着皮。
他的动作很慢,很仔细。一长条苹果皮,从头到尾,一点都没有断。他削好苹果,又用小刀切成很小很小的块,放进一个碗里,用勺子捣成了泥。
他做这一切的时候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但那份专注和耐心,却让人动容。
内心独白:这就是他说的“看望长辈”。如果他和我老婆真有什么不清不白的关系,他有必要在我面前演这出戏吗?我看不懂。我越是想把他定义成一个坏人,就越是发现他和我预设的形象对不上号。
他用勺子舀起一点苹果泥,凑到老太太嘴边,轻声说:“妈,吃点东西。今天苹果甜。”
老太太没有任何反应。
他又试了一次,声音更加温柔。“妈,我是刚子。张嘴,啊……”
老太太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,但还是没有张开。赵刚没有不耐烦,他放下碗,拿起一块热毛巾,轻轻地擦拭着老太太的脸和手。他的动作,轻柔得像是在呵护一件瓷器。
我站在门外,像个偷窥者,心里五味杂陈。我来是想抓证据的,是想看到不堪的一幕来证实我的猜想。可我看到的,却是一个儿子对母亲最朴素的孝顺。
就在这时,赵刚好像察觉到了什么,猛地回过头。我们的目光,隔着门缝,再一次撞在了一起。
他的眼神里,没有了之前的平静,而是闪过一丝锐利和警惕。他站起身,快步走了出来,然后轻轻地带上了病房的门。
“你来干什么?”他把我拉到走廊的角落,压低了声音,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怒意。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情绪激动。
“我……我来看看。”我有些底气不足。
“看什么?看我家的笑话吗?”他逼近一步,身上那股机油味更浓了,“李先生,这是我的家事,和你没关系,和淑琴也没关系。我请你,马上离开这里。”
“怎么会没关系?”我被他的态度激怒了,“我老婆为了你妈,骗我说公司团建。你目前跟我说没关系?”
“她只是……她只是心善。”赵刚的眼神黯淡下去,声音也低了下来,“她不该瞒着你,这是她的不对。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
“那是什么样?”我咄咄逼人。
内心独白:我像一个疯子,拼命想从他嘴里撬出一个我想要的答案。可他的反应,却像一堵墙,让我所有的力气都无处发泄。我开始怀疑,是不是我自己错了?错得离谱?
赵刚看着我,嘴唇动了动,最终却什么也没说。他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,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无奈。
“你走吧。”他说,“算我求你。别在这里,让我妈……走得不安静。”
他说出最后几个字的时候,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arle的颤抖。我心里一震。走得不安静?难道说……
我再也问不下去了。看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,和他身后那扇紧闭的病房门,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闯入别人悲伤世界的恶棍。
我没有再说一句话,转身默默地离开了。
走出医院,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城市的霓虹灯一盏盏亮起,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迷茫。
我来大同,是为了寻找一个背叛的真相。可我找到的,却是一个沉默的匠人,和一个躺在病床上的母亲。
王淑琴,你到底瞒着我什么?我们之间,到底隔着怎样一段我不知道的过去?
内心独白:我的愤怒,在那个破旧的厂房里被消解了一半,又在这个冰冷的医院走廊里,被彻底击溃了。剩下的,只有巨大的疑问和深深的疲惫。我像一个在海上迷航的水手,看不到灯塔,也找不到方向。
第4章 无法接通的电话
我找了家小旅馆住下,房间很小,窗外就是一条喧闹的马路。
我把自己扔在床上,盯着天花板,脑子里乱糟糟的。赵刚削苹果的样子,他和他母亲在病房里的样子,他最后那句“让我妈走得不安静”,像电影画面一样,在我脑海里反复播放。
我拿出手机,翻出王淑琴的号码。我想给她打电话,想质问她,想让她给我一个解释。但我的手指悬在拨号键上,却迟迟按不下去。
我怕。我怕听到她的声音,怕我们的对话会变成一场歇斯底里的争吵,怕最后那层窗户纸被捅破,一切都无法挽回。
内心独白:二十多年的婚姻,就像一件精美的瓷器。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捧着,生怕磕了碰了。可目前,上面已经出现了一道裂痕。我不敢去碰,怕它“哗啦”一声,碎得再也拼不起来。
我烦躁地坐起来,点了一根烟。烟雾缭绕中,我想起了我和淑琴刚认识的时候。那时候,我们都在一家国营厂上班,我是技术员,她是广播站的播音员。她声音好听,人也长得美丽,是厂里许多小伙子的梦中情人。
是我,用半年的工资买了一台录音机,录下她所有的广播,才追到她的。我们结婚的时候,什么都没有,就一间单位分的十几平米的单身宿舍。可那时候,我们很快乐。
这些年,我的事业越来越顺,职位越做越高,钱也越赚越多。我们换了大房子,买了车,儿子也上了大学。我以为,我给了她最好的生活。可我有多久,没有好好听她说过话了?
我每天回家都很晚,吃完饭就看电视或者玩手机。她跟我说邻里间的琐事,我会觉得烦。她跟我说她想去学个插花或者烘焙,我觉得是浪费时间。我总说,我养着你就行了,你别折腾了。
是我,亲手把我们之间的距离,拉得越来越远。
内心独白:我总以为,男人在外面打拼,赚钱养家,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。我忘了,家不是公司,不需要KPI。家需要的,是陪伴,是倾听,是理解。这些最基本的东西,我好像都忘了。
我掐灭了烟,终于下定决心,拨通了她的电话。
电话响了很久,就在我以为她不会接的时候,那边传来了她熟悉的声音。
“喂,建华?”她的声音听上去有些疲惫。
“你在哪儿?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
“在……在酒店啊。我们明天就回去了。”她顿了一下,似乎有些心虚。
“哪个酒店?”我追问道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。“建华,你怎么了?查岗啊?”她的语气带上了一丝不悦。
“王淑琴!”我再也忍不住了,声音陡然拔高,“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?你根本不在什么景区,你在大同!我说的对不对?”
电话那头,是死一般的寂静。我能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。
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?”过了很久,她才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问道。
“我怎么知道?我他妈的也在这里!”我几乎是吼出来的,“我在大同!我看到你朋友圈里的那个碗了!王淑琴,你为什么要骗我?那个赵刚,到底是你什么人?”
“建华,你听我解释,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……”她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“我不想听!”我粗暴地打断她,“我只问你,你和他,到底是什么关系?”
“我们……我们是朋友。”
“朋友?”我冷笑一声,“有为了一个普通朋友,骗自己老公,跑一千多公里来看他妈的吗?你当我是傻子吗?”
“建华,你别这样,你听我说……”
“我不听!”我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在往头上涌,“王淑琴,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。你目前就告知我,你和他,到底有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?”
电话那头,又是长久的沉默。这沉默,像一把刀,一刀一刀地割着我的心。
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,她终于开口了,声音无比清晰,也无比冰冷。
“李建华,在你心里,我就是这么一个不堪的人吗?”
“在你心里,我们二十多年的感情,就这么经不起一点风浪吗?”
“你既然不信任我,又何必来问我。”
说完,她挂断了电话。
我再打过去,已经是“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”。我知道,她把我拉黑了。
我颓然地坐在地上,手机从手中滑落。房间里一片死寂,我只能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声和狂乱的心跳声。
内心独白:完了。一切都完了。我把事情搞砸了。我像一个手持利刃的莽夫,把我们之间最后那点信任,也亲手斩断了。我想要的不是这个结果。我只是……只是太害怕失去她了。
第5章 尘封的往事
第二天,我是在头痛欲裂中醒来的。昨晚,我几乎一夜没睡。
天亮后,我做了一个决定。我要再去见一次赵刚。这一次,不是质问,不是审判。我只想知道一个真相。王淑琴不肯说的真相,或许他会告知我。
我再次来到那个破旧的厂房。赵刚依旧在那个巨大的车床旁,敲打着那个不知名的零件。看到我,他并不惊讶,只是停下了手中的活。
“我们谈谈吧。”我说,声音沙哑。
他点了点头,把我带到了厂房角落的一个小办公室。办公室很简陋,一张桌子,两把椅子,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工厂结构图。
“你想知道什么?”他给我倒了杯水,开门见山。
“所有。关于你,关于淑琴,关于你们的过去。”我看着他的眼睛,一字一句地说。
赵刚沉默了很久,目光投向窗外那片荒芜的厂区,眼神变得悠远。
“我和淑琴,是邻居,也是同学。”他缓缓开口,像是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。
“我们都住在红旗厂家属院。我爸是厂里的八级钳工,她爸是厂里的工程师。我们两家关系很好。那时候,厂里的生活很简单,我们一起上学,一起放学,一起在厂区的空地上玩。”
他的叙述很平淡,但我能感觉到那份深埋在岁月里的情感。
“后来,我们长大了。情窦初开的年纪,许多事情,就自不过然地发生了。”他说到这里,顿了一下,看了我一眼。
我的心,又被揪紧了。
“我们……在一起过。”
虽然早已猜到,但亲耳听到他承认,我的心还是像被针扎了一下。
“那时候,我们以为会永远在一起。考同一所大学,毕业后回同一个厂,结婚,生子,就像我们的父辈一样。”赵刚的嘴角,泛起一丝苦涩的笑意。
“但生活,总是不按你想的剧本走。”
“高三那年,我爸在一次设备检修中,出了事故。为了抢救一个年轻的徒弟,他被一个几百斤重的零件砸中了腿。”
“他没死,但腿废了。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八级工,变成了一个需要人照顾的残疾人。家里的天,一下子就塌了。”
“我爸心气高,受不了这个打击,脾气变得很暴躁。家里所有的重担,都压在我妈一个人身上。为了照顾我爸,也为了供我读书,她白天在食堂上班,晚上去外面打零工,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”
“我高考失利了。不是我考不上,是我不敢考。我知道,家里已经没钱供我上大学了。我放弃了,选择进厂当了一名学徒工,子承父业。”
内心独白:我从没听淑琴讲过这些。在我的印象里,她的过去是一片空白。原来,在她认识我之前,还有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。我感到一阵嫉妒,也有一丝莫名的心疼。
“淑琴考上了大学,去了省城。我们成了异地恋。那时候通讯不方便,只能写信。一开始,我们每周一封。后来,一个月一封。再后来……”
赵刚没有再说下去,但结果不言而喻。
“是我提的分手。”他低着头,声音很轻,“我知道,我给不了她想要的未来。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长痛不如短痛。”
“分手那天,她从省城跑回来,在厂门口等了我一夜。我没去见她。我让工友告知她,我跟车间的女工好上了。”
“我记得那天下了很大的雨。我躲在车间里,听着外面的雨声,心都碎了。”
他说完,办公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,一个年轻的女孩在雨中绝望地等待,一个同样年轻的男孩在暗处心如刀割。
“后来,她大学毕业,分到了你们厂。再后来,就听说她结婚了。”赵刚抬起头,看着我,眼神里有一种释然,“她嫁给你,过得很好。我知道,我当年的选择,是对的。”
内心独白:我一直以为,我是淑琴的初恋,是她唯一的依靠。原来,在她心里,一直藏着这么一个人,这么一段往事。我不知道该庆幸,还是该悲哀。
“那这次呢?她为什么来找你?”我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。
“由于我爸。”赵刚的眼神黯淡下来,“我爸当年出事,淑琴她爸,也就是我未来的岳父,是当时的现场总指挥。他一直觉得,是我爸的牺牲,才保住了厂里的设备和那个年轻徒弟。这份恩情,他们家记了一辈子。”
“前段时间,我妈查出了脑瘤,晚期。手术费要一大笔钱。我这些年修机器,没攒下多少钱。我把房子卖了,还是不够。”
“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。她给我打了电话,问我需不需要帮忙。我拒绝了。我们已经二十多年没联系了,我不能再给她添麻烦。”
“可她还是来了。她带着钱来的。她说,这钱不是给我的,是替她爸,还当年我爸的人情。”
“我没要。我们赵家的人,有骨气。就算是死,也不能欠别人的。”赵刚的语气,斩钉截铁。
“她没办法,就留下来,帮我一起在医院照顾我妈。她说,钱你不要,总不能不让我这个晚辈尽点孝心吧。”
“前天,医生说我妈时间不多了。她才走的。走之前,她把剩下的钱塞给了我。她说,‘赵刚,算我求你,让阿姨走得体面一点。’”
赵刚讲完了。我坐在那里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真相,像一把锋利的刀,剖开了我所有的猜忌和怀疑,也剖开了我的自私和狭隘。
我以为我抓到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,一个背叛的证据。到头来,却只是一个关于情义、责任和尊严的,略带伤感的故事。
第6章 平凡的尊严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个小办公室的。
赵刚的故事,像一块巨石,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。我脑子里一片混乱。淑琴的谎言,赵刚的坚持,那段被尘封的往事,所有的一切交织在一起,让我喘不过气。
我没有回旅馆,而是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。我路过古老的华严寺,看到虔诚的香客在佛前跪拜。我路过喧闹的鼓楼,看到年轻的情侣在街头拥吻。这座城市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,自己的悲欢。
而我,像一个局外人,迷失在了别人的故事里。
内心独白:我究竟在气什么?气淑琴的隐瞒?还是气在她心里,还有另一个男人的位置?或许,我气的,是自己的无能。我自以为给了她富足的生活,却没能给她最需要的理解和尊重。在情义面前,我的那些物质上的优越感,显得那么可笑和苍白。
不知不觉,我又走回了“北方机械”那个破旧的厂区。厂房里,那“当……当……”的敲击声,依然在继续。
我鬼使神差地又走了进去。
这一次,我没有站在远处,而是走到了赵刚的身边。他正在打磨一个齿轮,神情专注得像一个正在创作的艺术家。火花四溅,映着他那张布满汗水的脸。
我注意到,他用的工具,许多都超级老旧了,但被他擦拭得锃亮。他身边的桌子上,放着一本厚厚的、已经翻得卷了边的机械图册。
“这些老机器,早就没人用了吧?修好了又有什么用?”我忍不住问。
赵刚没有停下手中的活,头也不抬地说:“有些东西,在别人眼里是废铁。但在需要它的人眼里,是宝贝。”
“前几天,有个内蒙的矿场,一台三十年前的老钻机坏了。德国的专家来看了都直摇头,说没配件,修不了,让他们买新的。一台新的,上千万。”
“后来他们找到我。我花了一个星期,给他们重新做了个零件,换上去,机器又转起来了。他们给了我五万块钱。这五万块,就是我妈的救命钱。”
他说得云淡风轻,我却听得心头一震。
“你这手艺,完全可以去大公司当个技术总监,拿几十万年薪,何必守着这个破厂房?”
赵刚终于停下了手中的活,他关掉机器,用那双满是油污的手,擦了擦额头的汗。
“我爸临走前跟我说,‘刚子,做人,得对得起手里的这把锤子。’这厂里,有我爸一辈子的心血。这些机器,都是他当年亲手调试的。我守着它们,就像守着我爸一样。”
“再说,我走了,那些用老机器的,怎么办?他们没钱换新的,就只能停产,工人就得下岗。我在这里,至少能让他们多撑几年。”
他拿起桌上那个搪瓷茶缸,猛地灌了一大口水。
“人活一辈子,总得有点念想。钱是好东西,但不能为了钱,把根都忘了。”
内心独白:不能为了钱,把根都忘了。这句话,像一记重锤,狠狠地敲在了我的心上。这些年,我为了升职,为了赚钱,陪客户喝酒喝到胃出血,点头哈腰,说尽了违心的话。我得到了许多,但也失去了许多。我有多久,没有像赵刚这样,理直气壮地,为了一个“念想”而活了?
我看着他,看着这个沉默的匠人,这个为了一个承诺,为了父亲的遗愿,为了那些素不相识的人,而坚守在这片废墟里的男人。我心里那点可怜的优越感,瞬间荡然无存。
我忽然清楚了淑琴。她来这里,不仅仅是为了还一份人情,更是为了守护一份她所敬重和怀念的东西。那是一种在我们的生活中,已经越来越稀缺的东西——平凡的尊含和匠人的风骨。
而我,却用自己那颗肮脏、狭隘的心,去揣度她,去侮辱她。
我感到一阵深深的羞愧。
“对不起。”我低声说。这两个字,发自肺腑。
赵刚愣了一下,随即摆了摆手,脸上露出一丝憨厚的笑容。“没什么对不起的。换成是我,我也会跟你一样。”
他顿了顿,又说:“淑琴是个好女人。好好对她。”
我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就在这时,我的手机响了。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。我接起来,电话那头,传来一个焦急的女声。
“请问是李建华先生吗?我是市三院的护士。刘桂香的家属赵刚,刚刚晕倒在病房了!”
第7章 三个人的和解
我赶到医院的时候,赵刚已经醒了。他躺在走廊的临时病床上,正在输液。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。
医生说,他是由于连日劳累,加上营养不良,才会晕倒的。没什么大碍,休憩一下就好。
我看着他那副虚弱的样子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这个像钢铁一样坚硬的男人,终究也是血肉之躯。
他看到我,挣扎着想坐起来。
“你躺着吧。”我按住他,“医生说你得休憩。”
他没再坚持,只是把头转向了十三床病房的方向,眼神里充满了担忧。
“我妈……她怎么样了?”
“护士看着呢,没事。”我安慰道。
我们沉默地坐着。医院走廊里人来人往,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,却反而让我们的沉默显得更加突出。
“你……给她打个电话吧。”过了很久,赵刚忽然开口,“她肯定也急坏了。”
我知道他说的是淑琴。我的心,又是一紧。
我拿出手机,解除了黑名单,找到了淑琴的号码。我犹豫了很久,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
赵刚看着我,说:“告知她,我没事。也告知她,你都清楚了。”
我深吸一口气,按下了拨号键。
电话几乎是秒接。
“喂?”淑琴的声音充满了焦虑和不安,“建华?是你吗?你怎么样了?赵刚他……他怎么样了?”
她一连串的问题,让我鼻子一酸。
“我没事。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,“赵刚也没事,就是累倒了,在输液。”
“那就好……那就好……”电话那头,传来了她如释重负的抽泣声。
“淑琴,”我叫着她的名字,声音有些哽咽,“对不起。”
电话那头,哭声更大了。那哭声里,有委屈,有释放,也有原谅。
“你在哪儿?我去找你。”我说。
“不用了。”她止住哭声,“我已经在路上了。我买了最早一班来大同的飞机。”
挂了电话,我坐在赵刚的病床边,心里那块压了几天的大石头,终于落了地。我们都没有再说话,但彼此心里都清楚,有些结,已经解开了。
内心独白:原来,信任的重建,有时候只需要一句“对不起”和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。我以前总觉得,男人就该是家里的顶梁柱,就该强势。目前才清楚,真正的强劲,是懂得示弱,是懂得承认自己的错误。
下午,淑琴赶到了医院。她瘦了,也憔悴了。看到我,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我们没有拥抱,也没有过多的言语,只是相视一笑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然后,她走到赵刚的病床前。
“刚子,你这是何苦呢?”她看着他,心疼地说。
赵刚笑了笑,那笑容里,有歉意,也有释然。“让你担心了。”
那天下午,我们三个人,就在医院的走廊里,进行了一场迟到了二十多年的谈话。我们聊起了过去的红旗厂,聊起了家属院里的那棵老槐树,聊起了赵刚的父亲,也聊起了淑琴的父亲。
许多我不知道的往事,像拼图一样,一块块地被拼接完整。我终于清楚,他们之间,有一种超越了爱情的情感。那是一种由共同的记忆、父辈的恩情和对彼此人格的尊重交织而成的,牢不可破的联结。
我不再嫉妒,也不再怀疑。我甚至,有些感激赵刚。是他,让我看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,有情有义的王淑琴。
傍晚的时候,护士通知我们,刘桂香老太太的情况,不太好了。
我们三个人一起走进了病房。老太太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。赵刚握着她的手,把脸贴在上面,眼泪无声地滑落。淑琴站在他身后,轻轻地拍着他的背。
我站在门口,看着眼前的这一幕,心里百感交集。
那天深夜,老太太安详地走了。
我们帮着赵刚处理了后事。没有繁琐的仪式,一切从简。就像她来的时候一样,走的时候,也很安静。
离开大同的前一天,我把一张银行卡塞给了赵刚。
“这里面有二十万。不是给你的,也不是借给你的。算是……我替淑琴,买下你手里的那份匠心。”我说。
赵刚看着我,没有拒绝,也没有接受。
“李大哥,”他第一次这样叫我,“淑琴跟了你,是她的福气。”
我笑了。我知道,我们之间,也和解了。
回家的飞机上,我和淑琴一路无话。快要降落的时候,她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。
“建华,后来,我们有什么事,都别瞒着对方,好吗?”
“好。”我握住她的手,紧紧地。
回到家,一切如常,又好像什么都变了。我不再觉得她做的家务是理所当然,我开始学着和她聊天,听她讲那些我以前觉得无趣的琐事。我甚至,开始对她那些关于传统手工艺的文章,产生了兴趣。
一天晚上,我看到她在浏览一个旅游论坛。我凑过去看,她正在写一个帖子。
标题是:去了趟山西大同,感觉这里和网上说的不一样,3个疑问有知道的吗?
正文是:
1. 为什么大同这座城市这么干净,天这么蓝,和传说中的“煤都”完全不一样?路上的行人看起来都很悠闲,一点也不像网上说的那么粗犷。
2. 为什么大同的刀削面,就是简单的面、汤和几片肉,却能做得那么好吃?是不是最简单的食材,才最考验功夫?
3. 为什么城西那边那么多破旧的老厂房,不拆掉盖商品房,而是留着?听说还有人在里面修一些几十年前的老机器,真的有人需要这些东西吗?
我看着这三个问题,笑了。我知道,这三个问题,她心里早就有了答案。
这不仅仅是关于一座城市的疑问,更是关于一段人生,一份情义,和一种尊严的叩问。
而我,也很庆幸,陪她一起,找到了答案。
内心独白:家,到底是什么?以前我以为,家是我打拼的后方。目前我清楚,家,是战场,也是港湾。它需要我们一起去战斗,去守护,去理解,去包容。这一次大同之行,像是我婚姻里的一场大修。虽然过程惊心动魄,但好在,最重大的那个零件,我们没有弄丢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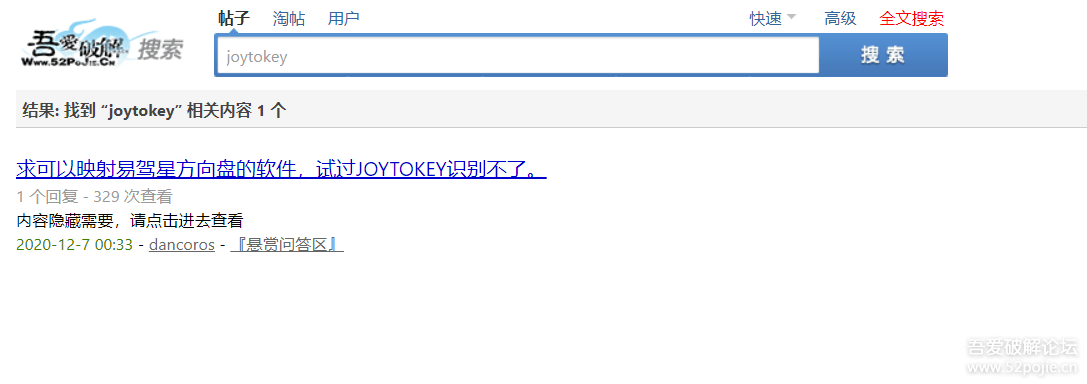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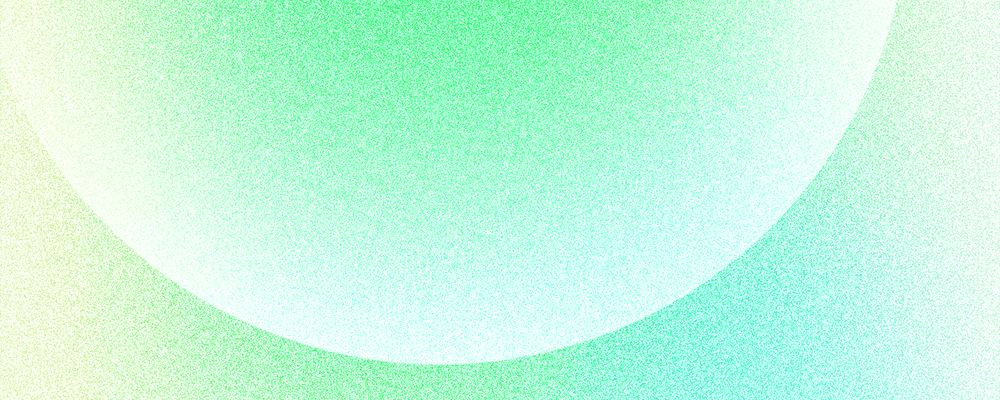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暂无评论内容